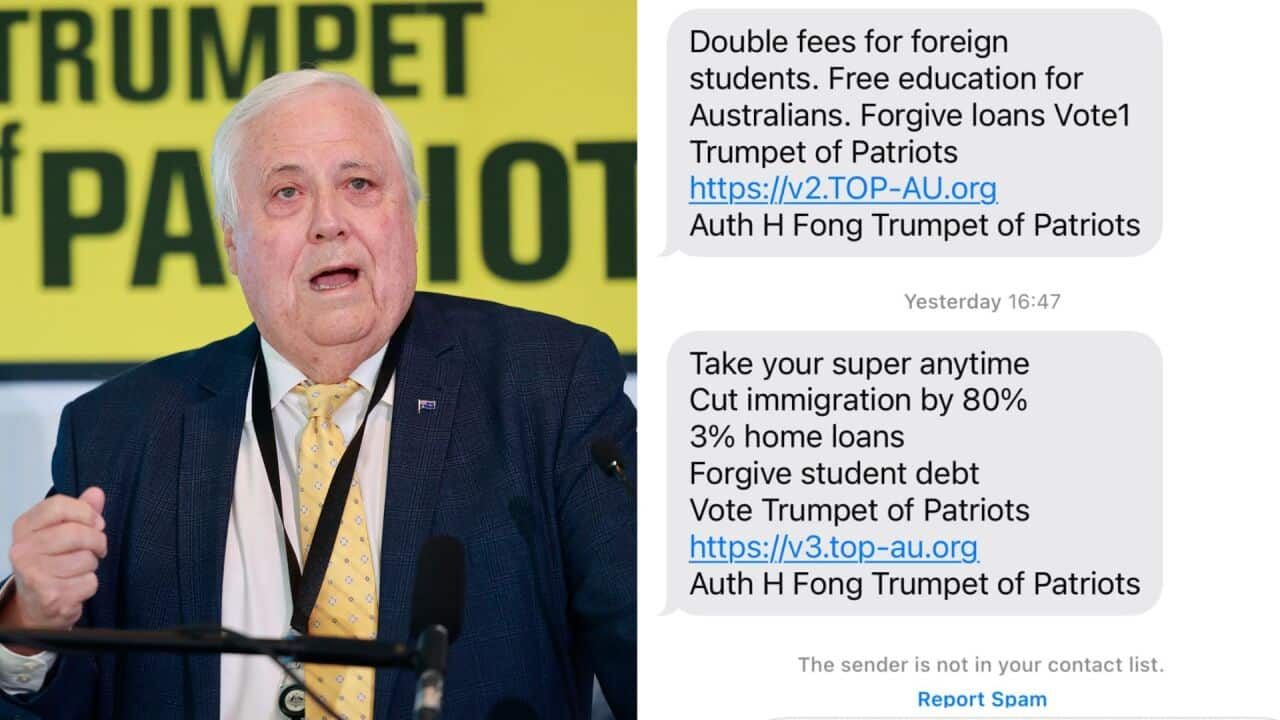4月25日是澳新军团日(ANZAC Day),这是纪念所有曾“在战争、冲突、和维和行动中服役和牺牲的人”的日子,也是纪念“所有曾遭受战争之苦将士”的一天。
其实,顾名思义,澳新军团日最初为纪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的澳新军团成员而设立的节日。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加里波利(Gallipoli)登陆,遭到了土耳其守军的激烈攻击。至年底,2.8万人的澳新军团,有8709人死亡。
这是澳大利亚军事史上一块不能磨灭的伤疤。但当我们在纪念澳新军团日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曾做出杰出贡献的华人军人们——在宏大的战争叙事中,这个独特的群体往往被忽略了。
28%华人应征入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裔澳大利亚人非常迅速地响应了保卫家园的征兵号召。第一个加入澳大利亚帝国军的华裔澳人是Albert Victor Chan。战争爆发两周后,他就被列入了入伍名单。
许多人克服了参军的歧视和障碍,与其他澳大利亚人一起,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澳华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的志愿研究员、Edmond Chiu A.M.教授接受SBS中文普通话采访时指出,当时全澳有200多名华裔澳人应征入伍,其中54人因战争或伤病,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已经确认了278个加入了澳大利亚第一帝国军,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裔澳大利亚人。”
“我已经确认了278个加入了澳大利亚第一帝国军,并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华裔澳大利亚人。”

位于墨尔本的澳华历史博物馆。 Sourc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第一批在加里波利作战的澳新军团中共有32名澳大利亚华裔军人,其中5人在加里波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他一些人)感染了严重的肠热病和痢疾,不得不被遣送回澳大利亚。”
他们实际上是参加加里波利之战的澳新军团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Chiu教授说,1911年澳大利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澳有华人血统的人为2743人,他们被归类为“天生的英国国民(Natural Born British Subjects)”。
这其中处于“符合征兵年龄”的人数为987人,因此278名华裔澳人入伍是相当大的一个比例——这占到当时澳大利亚华裔人口的28%。
孤松
Chiu教授向我们讲述了一位年轻的华裔士兵 James Albert Sooning的故事。他曾是一名煤气装配工,不幸的是,他没能活着从加里波利回来。 “来自Townsville的Sooning, James Albert在1915年1月18日入伍,当时22岁。在那之前,他是一位民兵。”
“来自Townsville的Sooning, James Albert在1915年1月18日入伍,当时22岁。在那之前,他是一位民兵。”

Chinese ANZAC soldier SOONING , James Albert Sourc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他于1915年4月16日登船,6月16日抵达加里波利并加入步兵第15营,参加了8月的进攻。8月8日,他在战斗中阵亡。
“他被埋在了战场上,但是后来,人们却找不到他的坟墓。由于他的遗体不知道被埋葬在哪里,如今,他在孤松陵园被人们纪念。”
孤松(Lone Pine)陵园,又叫孤松公墓或失踪者纪念馆,是澳大利亚纪念加里波利战役的主要纪念场所。这里祭奠丧生在战争中的3268名澳大利亚人和456名新西兰人,以及葬身于大海的960名澳大利亚人和252名新西兰人。
它以地中海地区的一棵松树命名,因为1913年问世的流行歌《孤独松树之歌The Trail of the Lonesome Pine》,故也被称为“孤松”。这里原本有好几棵树,除了这一棵之外,其余的都被土耳其军队砍倒,为战壕提供木材。
在早期的一场战斗中,它被摧毁了。人们将从土耳其加里波利带回的一颗松果种植在澳大利亚,后来,这颗孤独的松树成为人们纪念阵亡将士的象征。 还有一位叫Charles Tucker(aka Ah Tuck, Charles)的华裔士兵同样永久长眠在了加里波利战场上。
还有一位叫Charles Tucker(aka Ah Tuck, Charles)的华裔士兵同样永久长眠在了加里波利战场上。

The Honour Roll of Chinese and Chinese-Australian soldiers served in WWI. Sourc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Charles Tucker实际上姓Tuck。他来自新州,但不知为何,他把出生地标记为珀斯。1914年12月30日,24岁的他应征入伍,是16营的一员。”
“他也(在战斗中)受伤了,且伤势很重,并于1915年8月11日在伤亡运输站去世。”
后来人们发现,他的姓其实是Ah Tuck,因为他的兄弟写信给军队,并解释了他的背景细节。
1915年,一位19岁有着华裔血统的火车司机在昆州入伍,但是他的生命停止在了他到达战场后的第六天。
“另一个华人士兵William George Lampan出生在昆州的Charters Towers。1915年3月,年满19岁的他在昆州入伍,并于1915年6月12日从布里斯班起航,8月2日在加利波利加入步兵第15营。” “仅仅在抵达六天后,他就在1915年8月8日的孤松战役中阵亡。”
“仅仅在抵达六天后,他就在1915年8月8日的孤松战役中阵亡。”

Chinese ANZAC soldier William George Lampan Sourc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孤松之战是加利波里战役中极其惨烈的一战。
1915年8月16日,澳大利亚第二野战救护队的一名叫维克托·莱德劳(Victor Laidlaw)的士兵记录了悲惨的场景:
“透过望远镜看得很清楚,有很多尸体……土耳其人躺在5英尺深的战壕里,我们的伙伴不得不站在尸体上作战。炸弹把尸体弄得更糟,跳蚤到处都是,巨大的蛆虫开始出现……”
Chiu教授说:“William也是孤松陵园的一位被纪念者,因为,人们也没有找到他的埋骨之处。”
“并无差异”
这些参军的华裔士兵大多数出生在澳大利亚。他们很多人是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期间移民到澳大利亚的华人的后裔。
欧洲裔白人担心华人会抢“生意”,再加上部分地区华人人口不断扩大,这使得当时种族关系颇为紧张,进而催生了针对华裔的歧视性立法。
其中一个例子是1909年的《国防法(Defence Act 1909)》,这一法案宣布“非欧洲血统或欧洲后裔”的人不能参军。
不过,这并没有停下华裔将士参军的脚步。Chiu教授认为,在平民中,针对华人的歧视的确存在,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歧视延续到了军中。
“他们写下了出生地,他们出生在澳大利亚。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被军队接受了,虽然有(法律)规定他们不应该被接受。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提出应征入伍时因为身为华裔而被拒绝,但他们大多数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军官们不得不做出决定,接受了他们。”
尽管存在针对华裔澳大利亚人的歧视,但Chiu教授认为,参加澳新军团的华裔将士和其他澳大利亚人并无差异。
“他们与其他的澳大利亚军人没有什么不同。一战期间,他们做了澳大利亚帝国军所要求做到的一切。”
“我能确定一战中没有歧视,这些华裔军人都是优秀的士兵,澳大利亚士兵接受他们作为伙伴,和其他人没有区别。战争中,他们被认可,且他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收到了英勇勋章。”
Chiu教授告诉我们,有23名华裔士兵获得了英勇勋章,其中有些人获得了多项勋章的嘉奖。 其中,获得荣誉最高的是Caleb Shang,他获得了两次殊功勋章,以及一次军事勋章。
其中,获得荣誉最高的是Caleb Shang,他获得了两次殊功勋章,以及一次军事勋章。

Chinese ANZAC soldier Billy Sing Source: Museum of Chinese Australian History
次之的是著名的加里波利狙击手沈比利(Billy Sing)。据记载,在战场上,他杀敌约200人。沈比利的父亲是来自上海的放牧人,母亲则是一名英国护士。他获得了一次殊功勋章以及比利时国王授予的英勇十字勋章。
战后,从战场归来的华裔军人们回到社区中,有些人还成立了早期的华人社团。
“当他们从战场上回来,恢复了平民的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设法回到了他们的以前的职业,继续和华人社区打交道。有些人在华人社区生活得很好,也有少部分人被歧视,过得并不好。”
“有一些人得到了土地,比如著名的沈比利。但他得到的土地质量很差,他没法依靠这片土地生存。事实上,他死于贫困,尽管他实际上是一战中最被称道的华裔士兵。”
时至今日,我们铭记这段历史,尤其是了解华人在战争中的贡献非常重要。
Chiu教授说:“华裔澳大利亚人看待自己时,他们华人的一面和澳大利亚的一面同样重要。他们说,这是我的家,也是我的国家。因此,我会为她而战。”
一名士兵曾说:
如果澳大利亚对我来说是一个足够好的居住地,那她也是一个足够值得让我为之而战的国度。
“所以这实际上是所有那些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出生的人、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华人的一种情绪。他们有华人的文化和背景,但澳大利亚是一个值得他们守护的国家。二战时期也同样如此,他们也是这么做的,”Chiu教授说。
“因此,华裔澳人对这片土地的忠诚,在这里很好地体现出来——体现在我们已确认的278名参加了一战,和约1200名参加了二战的华裔将士身上。”